【編者按】蘇軾一生“如鴻風飛,流落四維”,仕途幾經浮沉,一代文壇盟主的影響力卻未見消減;壯浪縱恣于儒釋道三家思想,其心靈世界博大宏豐,兼擅詩、詞、文與書法、繪畫,乃至經學、史學、醫藥、水利等;最后“湛然而逝,談笑而化”……
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朱剛的《蘇軾十講》通過十一個主題串聯蘇軾的生命歷程,并將蘇軾置于歷史與文化的洪流中,并作精妙講解。經出版社授權,第一財經節選書中部分內容,以饗讀者。
中國傳統關于“謫仙”的說法,是很有意思的。仙人本來在天上(或在海中仙山),不知因為什么緣故,而被謫居人間。這樣的人當然與凡人有所不同,如果是女性,應該特別美貌,是男性的話就才華橫溢,而無論是男是女,氣質上都超塵脫俗,多少留著些仙人的氣息。這當然是令人向往的,但是另一方面,他們既是“謫仙”,那就多少具有跟世俗不合的傾向,在這個世界顯得另類,可能被向往而不易被認同,所以大抵不可能生活得幸福安寧。唐代李白有詩云:“世人不識東方朔,大隱金門是謫仙。”(《玉壺吟》,王琦注《李太白全集》第377頁,中華書局1998年版)這東方朔在漢代就是以“滑稽”聞名的,比較另類,所謂“世人不識”,就是不容易獲得認同。當然最有名的“謫仙”是李白本人,他一到長安,就被賀知章呼為“謫仙人也”。那是指他的天才,絕非凡人所能有。從此,這個稱號幾乎就專歸了李白,直到蘇軾出世,人們才意識到:又一個“謫仙”來了。我們的祖先就是以這樣特有的方式,來表達他們對天才的尊重。
至于蘇軾自己,肯定也接受這樣的說法,他在不少作品中暗示或明說自己是“謫仙”,我們且看比較晚期的一首詩。紹圣四年(1097)剛登上海南島的蘇軾,便在瓊州(今海南海口一帶)至儋州的路上遇見一陣“清風急雨”,于是作詩云:
四州環一島,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,如度月半弓。登高望中原,但見積水空。此生當安歸,四顧真途窮。眇觀大瀛海,坐詠談天翁。茫茫太倉中,一米誰雌雄。幽懷忽破散,永嘯來天風。千山動鱗甲,萬谷酣笙鐘。安知非群仙,鈞天宴未終。喜我歸有期,舉酒屬青童。急雨豈無意,催詩走群龍。夢云忽變色,笑電亦改容。應怪東坡老,顏衰語徒工。久矣此妙聲,不聞蓬萊宮。(蘇軾《行瓊、儋間,肩輿坐睡。夢中得句云:千山動鱗甲,萬谷酣笙鐘。覺而遇清風急雨,戲作此數句》,《蘇軾詩集》卷四十一)
詩的前半部分寫蘇軾飄落海外的境遇和感受。依北宋的政區劃分,海南島上有瓊州、崖州、儋州和萬安州四州,圍繞著島中央洞穴盤結的五指山。蘇軾自瓊州登島,先向西,再折向南,奔赴儋州,正好經過了島嶼的西北部,走了一條弧線。因為隔著大海望不到中原,四顧途窮,恐怕回歸無望,所以只好用戰國時的“談天翁”鄒衍關于“大九州”“大瀛海”的說法來排遣心情。按鄒衍之說,中國雖由九州組成,但大地上像中國這樣大的地方還有八個,合稱“大九州”,每一州都有一小海環繞,與別的州隔絕,而在這“大九州”之外,還有“大瀛海”環繞,那才是天地相接之處。如此說來,中國(中原)也只是海水環繞的陸地之一,也就是面積較大的島嶼而已,跟海南島的情形沒有根本的區別。雖然有大小之分,但對于整個宇宙來說,都只像太倉中的一粒米而已,誰還去管這些米的大小呢?后半部分,從“幽懷忽破散”以下,轉入描繪與想象。一陣天風吹來,山上的草木如鱗甲一般翻動起伏,山谷里回聲頓起,像笙鐘在酣暢地演奏。于是場面迅速改觀,變得雄渾浩蕩,而且一切都似乎活了起來,令詩人開始馳騁其豐富奇特的想象。他說,這是神仙們在天上飲酒,想起了昔日的同伴蘇軾,謫落人間已久,算起來快到回歸的日期了。所以他們派遣群龍前來,飛舞著興風行雨,來催蘇軾作詩。天上的云彩變化莫測,如夢一般,神仙們發出的笑聲變成了閃電。蘇軾于是洋洋自得,說神仙們看了詩后怕要覺得奇怪,我這衰弱的老頭怎么還能寫出如此精妙的詩句,自從“謫仙”下凡以來,仙宮里應該好久都沒有聽到這樣好的詩句了。
海上的風濤奇幻怪譎,東坡的神思更是天馬行空。所謂“喜我歸有期”,“久矣此妙聲,不聞蓬萊宮”,都是以“謫仙”自認的明證,而“歸”字所指的方向,當然是天上仙宮。
然而,這位“謫仙”對如此“歸”去的意義,卻也曾發出質疑,書寫在著名的《水調歌頭》詞中:
明月幾時有,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,又恐瓊樓玉宇,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間。
轉朱閣,低綺戶,照無眠。不應有恨,何事長向別時圓。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。但愿人長久,千里共嬋娟。
(蘇軾《水調歌頭·丙辰中秋,歡飲達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懷子由》,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卷一)
這是熙寧九年(1076)中秋節,喝醉酒以后,想念弟弟蘇轍而作。一開頭就以“謫仙”的口吻,向他原來的居所“青天”提問,想知道如今的天上是什么歲月,仿佛一個離家的游子詢問家鄉的消息。“我欲乘風歸去”,這“歸”之一字就非“謫仙”不能道,而“乘風歸去”的飄然灑脫,也符合人們對于“謫仙”的一般想法:他總有一天會厭離人間,回到天上去。因為他在人間是另類,遭遇不會很如意,他的宿命是“歸去”,這不單是一種絕妙的解脫,也是對使他不如意者的輕蔑和嘲弄:就讓你們枉自折騰去吧,他那里飄然歸去,你們傷害不到。
一個富有才華的人應該得到的尊重,如果在人間失去,那就一定會由老天來補償。所以,蘇軾越是顛沛流離,人們便越相信他是“謫仙”。他被貶謫黃州,世間便產生了他白日仙去的傳聞,這傳聞令神宗皇帝也深深為之嘆息(見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三百四十二,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條)。畢竟,他知道蘇軾是天才,這樣的天才世間不常有,而居然出現在自己領導的時代,無論如何應該珍惜的。類似的傳聞在蘇軾身后也被多次“證實”,宋徽宗把蘇軾列入“元祐奸黨”,禁毀蘇軾的作品,但被他迷信的一位道士,卻自稱神游天宮,看到奎宿在跟上帝說話,而這位奎宿就是“本朝之臣蘇軾也”(陳巖肖《庚溪詩話》卷上,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)。這道士不會不知道宋徽宗的政策,但他更明白,自己裝神弄鬼要博得別人相信,最好搬出蘇軾來,因為大家早就知道蘇軾“乘風歸去”,一定是在天上做神仙。
可是,蘇軾的詞意卻從這里開始轉折,即對“歸去”的意義發生質疑。天上雖有瓊樓玉宇,似乎令人向往,但毫無人間煙火,那也就是一片凄清寒冷,若“歸去”那里,恐怕也只成個顧影自憐的寂寞仙子。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:還不如留在人間。對于這一點,宋人也有傳說云,神宗皇帝讀到了這一句,大為放心道“蘇軾終是愛君。”(龍榆生《東坡樂府箋》卷一,該詞箋注引《坡仙集外紀》)他把不愿“乘風歸去”、愿意留在人間的蘇軾,理解為留戀君主。
這當然也不完全是自作多情,因為類似的表達法,在詩歌史上也蔚為傳統,如謝靈運詩云:“本自江海人,忠義感君子。”(謝靈運《詩》,逯欽立輯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宋詩》卷三,中華書局1983年版)杜甫詩云:“非無江海志,瀟灑送日月。生逢堯舜君,不忍便永訣。”(杜甫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,
《杜詩詳注》卷四,中華書局1979年版)意謂自己本來可以瀟灑江海、逍遙世外,只因為留戀君主,才決心投入政治,做個忠義的人。蘇軾自己在另一首詞中,也對天女“問何事人間,久戲風波”,表示“老去君恩未報,空回首,彈鋏悲歌”[蘇軾《滿庭芳》(歸去來兮),《東坡樂府箋》卷二],說“謫仙”因為要報“君恩”而暫不歸去,“愛君”的意思還是很明顯的。清代的評論家劉熙載就專門把這幾句跟“我欲乘風歸去”等句對比,說不如后者寫得含蓄(劉熙載《藝概》卷四《詞曲概》,《劉熙載集》第144頁,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)。看來,他對《水調歌頭》詞意的理解,與傳說中的宋神宗的看法相近。
不過在《水調歌頭》詞中,蘇軾說的明明是“人間”,這“人間”當然不是只有君主一人的。他用“人間”跟“天上”對比,說明“人間”的范圍很大。詞是因想念蘇轍而作的,關于“天上”“人間”的這番思量和討論,首先是用來安慰蘇轍:這人間的生活雖然不盡如人意,但天上也并非完美,而且可能情況更糟,相比之下,不如留在人間。所以,“人間”的含義首先應就具體的人生境遇而言,就眼前兄弟相離、互相思念而不能見面的生活情狀而言,如果可以由此聯想到君臣關系,那么也可以進一步推廣到所有人世生活。
(本文節選自《蘇軾十講》第七講《東坡居士的“家”》,標題為編者所擬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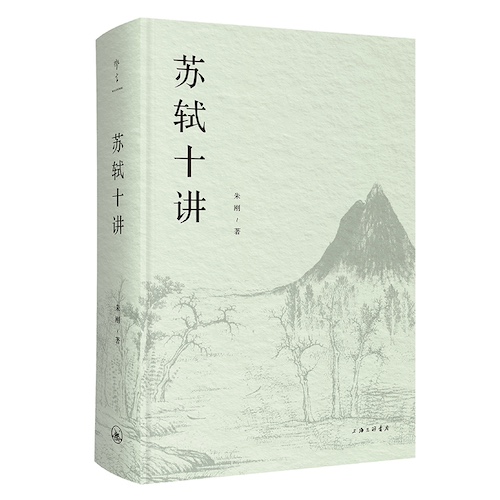
《蘇軾十講》
朱剛 著
上海三聯書店 2025年3月版
幫企客致力于為您提供最新最全的財經資訊,想了解更多行業動態,歡迎關注本站。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,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



